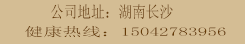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繁衍 > 卡尔维诺与后现代派文学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繁衍 > 卡尔维诺与后现代派文学

![]()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繁衍 > 卡尔维诺与后现代派文学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繁衍 > 卡尔维诺与后现代派文学
文/陈嘉禾
伊塔洛·卡尔维诺(—)
有这样一位作家,他生前做过一次脑外科手术,术后他的医生说,这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精妙复杂的大脑结构。
“他的书值得反复的阅读,他用他的创作实践展示了小说形式的无限可能”,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莫言这样把他引荐给读者。
他叫卡尔维诺,是当代意大利文坛 影响力的小说家,被称为“最有魅力的后现代大师”。
这两个标签直接指向了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并不那么容易回答: 个问题有关于意大利文学。“前巴黎时代”的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是西方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而文艺复兴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如今,若我们列举知名的意大利作家和作品,很多人可能依旧只能想到卜伽丘的《十日谈》以及但丁和他的《神曲》。当然,另外一些人还会想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只是把《爱的教育》当作一本“儿童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必读书目,是众多儿童文学读物中的佼佼者,而对其文学性没有进行过探究,直到有一天,当我发现绝大部分的意大利文学教材都会腾出一章来介绍《爱的教育》时,我才意识到这部书竟然是意大利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亚米契斯(一)
这件事着实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从《神曲》到《爱的教育》的过程是脱节的,而意大利似乎也早已不再是那个“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意大利文学是否有一种走下坡路的趋势,如果有,也一定与欧洲复杂的历史情况相关。当然,那些意大利文学的教材也并没有写到《爱的教育》便戛然而止了,后面还有两个名字,抒情诗人夸西莫多和小说大师卡尔维诺。
我想中国应该还是对意大利文学欠缺了解的。也许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并没有很多意大利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不过,卡尔维诺还算是有比较高的知名度。
第二个问题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学”。这本身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可以为其下不同的定义。而至于其产生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二战以后,有人认为是60年代。不过,“后现代主义”有几个公认的流派,例如“垮掉的一代”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之前的课里我也多多少少地提到过。
我试着归纳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几个特征:
不信任。这里的不信任不仅仅是对传统和权威的否定,也包括对既定规则和秩序的不满,甚至包括对未来“世界究竟会变成怎样”的悲观和不自信。在《青春》中,我讲“垮掉的一代”是一种深切的无力感而“迷惘的一代”则是一种反叛精神,但现在,我又觉得不仅仅是如此。或许“危机意识”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我今天想讲的《看不见的城市》中序言的一小段为例——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 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大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
菲利普·锡德尼(—)
英国诗人菲利普·锡德尼曾讲,“文学融合了哲学的观念和历史的事例并与艺术相结合,完成教育的目的。”因此,解读后现代主义,也必须把它放在“现代化”这一历史事件和视野之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产生这种“不信任”的根源: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工具理性、机械主义对想象力及情感感知的扼杀;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无不让人们开始怀疑和担忧,开始考虑当今时代的危机应该如何解决。
大众性。如同我在《精英入会仪式》中讲到的那样,由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读者的范围因而变得越来越庞杂和广泛。但这并不能说明后现代派的作品就容易读。因为“大众性”同时给了作家足够的自由去随心所欲地想象和写作,他们使用某些非连贯的、甚至颠覆性的语言,去构筑一个非常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世界。由此我们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它是作家自如的操纵和探索。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一类作家中读到他们的用心推敲,其中一点就体现在对结构的重视上。我曾读过一本文学史纲要,它将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昆德拉三人列在一起——我想他们应当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因为他们不仅是思想的好手,也是语言结构的巧匠。而且,凑巧的是,他们似乎都奉行一种“轻”的哲学和理念——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诗歌,都离不开对历史和时空的高度凝练与浓缩。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活之轻》中,提出了生命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里的那种“存在之轻”。
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则更是“轻”的信徒。他有一本叫《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讲稿,是他晚年在哈佛所作的讲座,也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理念的总结,而这些讲稿,无一不包含他对“轻”的独到理解:
“轻”首先是足够的留白,保留足够的神秘感而不必对一切作出解释:“我最难以释怀的,是听自己说话。这就是我为什么尽可能少讲。”“任何解释都会使神话贫化和窒息。”
“轻”其次是对于模糊和精确的权衡。据卡尔维诺说,意大利语是他 所知的方言,其“模糊”一词也有“可爱、有魅力”的意思,而这种魅力,大致就是某种高度的优雅,明朗却也能给人遐思。
而最重要的,“轻”由重而来。这里的“轻”不是一无所知的苍白和轻浮,而是充足积淀后所达到的“从容”的境界:“储蓄时间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储蓄得愈多,我们就愈经得起失去。风格和思想的快,尤其意味着灵活、流动和从容。”
因此对他而言,“在我向轻致意时,也隐含我对重的尊敬。”
在大致了解了这种理念后,读《看不见的城市》就不会感到十分费解了。
这本书有着散文诗集的诸多特点:瑰丽的想象和精致的文字,以及恰到好处的篇幅。但是,作为小说家的卡尔维诺还秉持着另外一个信念:“我相信一本书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不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完全没有情节的。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皇帝忽必烈的对话。每一座城市都隶属于可汗版图上的疆域,整本书则是马可·波罗对忽必烈作的关于旅行和考察的报告。这是一种奇妙到令人恍惚的想象,因为卡尔维诺将忽必烈塑造成了一个忧郁而善感的皇帝——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人的影射——他开始怀疑权力的价值,思考世界何时会毁灭,他生活在自己的记忆与欲望里却又为此烦忧。
“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在帝王的生活中,总有某个时刻,在为征服的疆域宽广辽阔而得意自豪之后,帝王又会因意识到自己将很快放弃对这些地域的认识和了解而感到忧伤和宽慰;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在黄昏时分袭来,带着雨后大象的气味,以及火盆里渐冷的檀香木灰烬的味道;会有一阵眩晕,使眼前绘在地球平面上的山脉与河流,在黄褐色的曲线上震颤不已;会将报告地方残余势力节节溃败的战绩卷起来,打开从未听人提过姓名的国王递来的求和书的蜡封。他们甘愿年年进贡金银、皮革和玳瑁,以换取帝国军队的保护;这个时刻的他,会发现我们一直看得珍奇无比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其腐败的坏疽已经扩散到远非权杖所能整治的程度,而征服敌国的胜利反而使自己承袭了他人的深远祸患,从而陷入绝望。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蚁蛀食的精雕细刻的窗格。”
而马可·波罗则是一个沉静的人,忽必烈汗难得一遇的知音。他们想象或见证了无数座城市的存在,甚至无需出声、只凭借手势和对物体的触感便能明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他们一同探讨了众多重要的生命命题,以至于到书的后面,他们的对话不再是对话,而是自己悟出的神谕——
“可汗:‘你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而旅行吗?你是为了找回你的未来而旅行吗?’
马可:‘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事物的陌生感,在你所陌生的不属于你的异地等待着你。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
这些城市有不同的类别,分别关于记忆、贸易、欲望、符号、眼睛,有的像一张蜘蛛网一样轻盈,有的甚至是靠一群男人对同一个女人的欲望而建造起来的。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还有一个了不起之处:因为它的轻盈,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往其中填充自己的见解,使它充满活力而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全书中我最喜欢的城市伊西多拉一样——
“这里的外来人每当在两个女性面前犹豫不决时总会邂逅第三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应该是相当具有魅力的,因为这座城市充满了巧合与可能性。不过,伊西多拉最打动我的还是下面的场景:“在梦中的城市,他正值青春,而到达伊西多拉城时,他已年老。广场上有一堵墙,老人们倚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记忆。”我想不管在何时何地何人,总能从中读出自己印象中的岁月光阴。
而书中的很多片段甚至带有先知的预兆和普遍适用的意味,就像马可·波罗讲遍了所有城市却唯独不谈自己的故乡威尼斯一样:“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的乡愁,不想提起,实际上却又与你形影不离。
另一座与欲望有关的城市叫珍诺比亚,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无需将珍诺比亚划归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城市范畴,按照这种类别区别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区分,则另有两类: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欲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另一类是要么被欲望抹杀掉,要么将欲望抹杀掉的城市。”这段话让我想到如今人们把城市划为三六九等、争相评选“ 幸福感城市”——我想卡尔维诺如果看到此情此景,也许会忍不住提醒我们:对幸福的向往不是对欲望的满足,“幸福感城市”需要保持对膨胀的幸福欲的清醒和克制。
书里描写的城市我无法一一穷尽,但这本书确实是我在年读到的很漂亮和精致的一本书,因此我在年的开头推荐给大家。 ,我想讲一讲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也是很多评论家谓之为内核的部分——此时,卡尔维诺似乎也按捺不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写道: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 种很容易:接受地域,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的风险大,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我们能想到的具有强烈关联的话,或许是卢梭的那句“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又或许是萨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狱”。对于生者的地狱究竟是否会出现,卡尔维诺有过短暂的乐观,但他紧接着以虚拟的方式迅速地解构了他自己刚刚作出的判断,因为他似乎是这样在表述——事实上不仅出现了地狱并且这个地狱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且我们对它的出现和形成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难以确切地知道是什么让卡尔维诺陷入这样的绝望——我猜是因为过于复杂的人性和新旧时代对立中遥遥无期的“进步”吧;但我们看到的却又不仅是绝望——无非那“免遭痛苦”的第二个办法和选择带来的希望,只能属于警醒、具有辨别力和开放包容的人。所以,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还需要一个词来描述它的特征的话,我想它或者可以是“倔强”:倔强地想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倔强地与一切抗衡。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陈嘉禾
你还可以看
进杜华的繁花世界
民间画院的那些事:文会·雅集·学术·培训·教育·公益
陈振濂谈
关于中国书店和琉璃厂近代史
编辑孙乐怡
——END——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
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周刊出品
扫一扫,带你飞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daimaoa.com/bdfz/115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