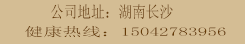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天敌 > 学者风采郭锡良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天敌 > 学者风采郭锡良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

![]()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天敌 > 学者风采郭锡良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天敌 > 学者风采郭锡良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
郭锡良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
华学诚刘静
摘要:郭锡良先生在训诂词汇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既有宏观的重大论题,包括先秦汉语词汇史、历史词汇与词义、汉语同源词、汉藏同源词;也有微观的具体研究,包括反训问题、古典诗文的字词考释、同义词辨析;还有应用的词典编纂。郭先生在训诂词汇研究中贯穿着下述理念:重视系统性和历史变异性,重视字词句落实和知人论世,重视词义发展和同义词辨析,重视汉语同源词和音义关系,重视汉藏同源词研究及其问题,重视先秦词汇发展史,重视词典编纂和词义的概括性,等等。郭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特点鲜明: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并重,系统性与历史变异性并重,同义词辨析与同源词探求并重,字词句落实与知人论世并重。郭先生在训诂词汇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史的一部分。
关键词:郭锡良研究训诂词汇中国语言学当代学术史
郭锡良先生是 语言学家,是当代语言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者。先生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是在古代汉语教材、汉语语法史、汉语古音学方面”(存稿p.1)①,但在汉字、词汇、方言、语言学史等领域也有不少贡献。本文拟就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谈一些学习心得,以此庆祝先生鲐背之寿,并向学界同仁请教。先生的训诂词汇研究文章,已经分别收入《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和《汉语研究存稿》之中。本文论述所据郭先生的文章均来自这两本论文集,不再检核始发书刊。
①郭锡良《汉语研究存稿·序言》。郭先生的《汉语研究存稿》,本文简称“存稿”;郭先生的《汉语史论集(增补本)》,本文简称“论集”。
郭锡良先生一重视系统性和历史变异性
“特别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和历时变异性,不孤立地观察问题,不以今律古”(论集p.2)①,这是贯穿在郭锡良先生汉语史研究各领域的基本理念,训诂词汇研究也是如此。
1.1“反训”现象是东晋郭璞 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怀疑甚至反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热烈讨论②,肯定和否定的意见都有,先生明确表示“反训不可信”。先生认为,一个词同时同地不可能具有正反两个意思,“反训”是“传统训诂学中早有争论,需要扬弃的见解”(论集p.)。
人们经常列举到的反训词,情况虽然不尽相同,先生认为都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清楚,并明确指出,“语言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古代的词义必须作出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训释,不应再沿用反训的说法”(论集p.)。③当然,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不是截然分开的,也有交叉的可能,尤其是有些词义演变完成所经历的时期比较长,这种共存现象就难以避免。所以先生说:“我不反对这种提法的合理性,但是反义的长期同时并存,这是需要考证的,要用大量材料来说明”(论集p.)。④
与郭先生争辩的张凡说,“所谓‘反训’,就是反义为训,即用反义词去解释词义,这是我国传统训诂学训释词义的一种方法”(论集p.)⑤。郭先生全面引用了齐佩瑢先生的相关论述,否定了张凡的观点(论集pp.-)。其实,古人并没有提出“反训”这个字面概念,“反训”连文使用是近现代的事情⑥,无论是“相反为训”还是“反训”,都不是指训诂方法;即使作为训诂条例,“反训”的实质仍然是同义相训。⑦
1.2《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句中的“毙”,从古到今都有人解释为“死”,这是错误的。郭先生对先秦十几部古书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先秦古籍中的‘毙’字,全部不能理解为‘死’;除了有些是通‘敝’或‘弊’以外,都只是‘倒下’的意思,既用于人、畜、物的具体的‘倒下’的动作,也用于抽象事物的‘衰败’,即‘倒下’的比喻义。”(论集p.)
先生还厘清了与此相关的文字问题和错讹滋生情况,指出:“今本先秦古籍中的‘毙’字,本作‘獘’。今本写作‘毙’,都是汉以后的人改易的。”(论集p.)先生论断,“毙”有“死”这个新义出现在汉代。《墨子·明鬼下》说“殪之车上”,王充《论衡·死伪篇》说“毙于车下”,先生因此说,“《论衡》改‘殪’为‘毙’,说明他是把‘毙’理解为‘死’了”(论集p.)。《论衡·祀义篇》有一段“毙”“死”共现的文字更是明证:“厉鬼举楫戈而掊之(指夜姑掌),毙于坛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验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厉鬼击之也,时命当死也。’”(论集p.)
“毙”不仅是从“獘”引申出来的,而且可能与“?、敝、弊”是同源词。“?”是破烂的衣服,引申之凡破烂的东西都可以叫“?”,于是产生了分化字“敝”;词义再扩大,生物因伤病而倒下也可以如此表示,因而又产生了分化字“獘”,“如果倒下,再也起不来,就是‘死’了”(论集p.)。先生特别强调,由此可以看到,“词义是有时代性的,也是有系统性的;训释词义一要有明确的时代观念,二要能从词汇的系统性来考察它与同源词的关系”(论集p.)。⑧
①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序言》。
②参见拙作《五十年来“反训”研究情况述评》(《昭通师专学报》年第3期)。遗憾的是,限于当时报刊发行、手工检索和所在大学的资料条件,本人撰写此文时没有见到郭先生的文章。
③郭锡良《反训不可信》。
④郭锡良《反训问题答客难》。
⑤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张凡〈反训辩〉内容要点》。
⑥清代陈玉澍在《尔雅释例》里较早提到“相反为训”这个说法,但这里的“训”不是动词,而是名词,“相反为训”就是“相反为义”;“反训”连文较早的使用者是陈独秀,他的《字义类例》第四章即题“反训”,参拙文《反训研究三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年第3期)。
⑦我曾经指出:“‘反训’或‘相反为训’不能理解为意义相反的词可以互相训释,即不是用反义词来解释词义的方法。认为可以用反义词来解释词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被解释词和解释词必须是同义或近义关系,即两个互相训释的词在意义上必须有共同之处,解释才会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认为反训条例的实质仍是‘同义相训’。”见拙文《反训研究三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年第3期)。
⑧郭锡良《说“毙”》。
二重视字词句落实和知人论世
王力先生在主编《古代汉语》时特别强调落实字、词、句,要求文选注释时贯穿始终。郭先生完全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指出“读古典作品,首先要落实字、词、句,进一步就要知人论世”(存稿p.)①。2.1王维有一首题《鸟鸣涧》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有编注者把“闲”注释为“安静”,把“桂花”当作桂树所开之花,先生认为这是不对的。“闲”和“静”的意思并不相同。“诗中‘人闲’与‘夜静’对举,更说明诗人在两句诗中要表达的重点是不同的”。(论集p.)诗中的“桂花”实际上是指代月光。“花”是“华”的六朝后起字,都有花朵、光华两音两义。隋唐时“光华”一般写作“华”,但仍有写作“桂花”来指代月或月光的(论集p.)。鸟鸣涧这个地方在春天没有桂花,先生为此提供了更多证明:湖南取名桂花或桂华的人往往是农历九月出生的;“《全唐诗》写到桂花的诗作,大致发映了一般人的认识,桂花是秋天才开花的”(论集p.);“岭南以北,长江、黄河流域,都只生长八、九月盛开的秋桂”(论集p.)。②在回答蔡义江先生的质疑时,郭先生补充了新证据。根据实际考察、方志有关辋川地理地形的记载、王维隐居终南山置备辋川别业后的生活处世交游情况和对《辋川集》内容的考索,先生认为,“《鸟鸣涧》所写的田园生活只可能出现在特定地理环境(东边山梁高耸的山谷)和时间条件(满月)中”(存稿p.)。先生的考证、诠释,不仅注重字词句落实,而且注重知人论世,包括山川地理、人文历史、植物天象等,可谓不刊之论。③2.2李白有一首题《望天门山》的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诗是描写诗人站在岸上还是站在船上望天门山的呢?先生认为解释成站在岸上是“让李白站错了地方”(论集p.)。先生指出,“两岸青山相对出”中的一个“出”字,说明整个诗是“动景”,“只能是李白乘船经过天门山瞭望两岸山景时才会有这样的感受”(论集p.)。先生认为,李白站在船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不是逆流而上,而是顺流而下。先生又从“知人知世”的角度进行了详尽考察、分析,使得释读坚碻不移。先生在考察了李白一生中曾经有哪些时段可能“过天门山”之后推断:“《望天门山》一诗是天宝十三载()李白从宣城往游广陵(今扬州市)时所作。”(论集p.)古人写诗追求“言志”,写《望天门山》时,李白“刚回江南不久,乘船再过天门山,深为长江浩浩荡荡、开山断石,一往无前的气势所感动,又喜看两岸青山,山峰连着山峰地成对迎面出现在顺流而下的帆船两旁”(论集p.),于是即景抒情。这一情感与李白同期写作的其他诗所表达的情绪是一致的,没有落魄离京漫游齐鲁梁宋之前过天门山不应有“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感情,安史之乱后年过六十以戴罪之身再过天门山也不可能有这种感情。④2.3传本古诗《孔雀东南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有一段描写兰芝被迫离开焦家的当天清晨起来梳妆打扮的情景:“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历代注家一直存在分歧,根本原因就是“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这一句误植而导致事理扞格难通。余冠英先生首先发现了错简,但移植位置并未令人满意。郭先生认为上面两句应当移植到“口如含朱丹”句后。先生分析道:“‘新妇起严妆’的内容不仅包括穿戴装束,还包括盥洗和涂抹化妆品。‘指如削葱根’是写盥洗后施用白色的手膏;‘口如含朱丹’则写施用了以朱砂为主要成分的口脂。梳妆、盥洗诸事毕后, 著裙。诗篇正是依次描写了兰芝梳洗打扮的过程,并且点明每件事都反复了四五遍。”(论集p.)这样校改之后,“或句句为韵,或隔句为韵,整齐不紊,这同全诗的押韵规则是一致的,足证这段诗原貌应是如此。”(论集p.)⑤先生细绎全诗,从事理上论证了如何正确移植错简,并从押韵上予以补证,从而恢复了古诗本来面貌,读来怡然理顺。①郭锡良《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②郭锡良《王维〈鸟鸣涧〉的桂花》。③郭锡良《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④郭锡良《李白在哪儿望天门山》。⑤郭锡良《〈孔雀东南飞〉的一处错简》。郭锡良先生与王宁先生、华学诚先生合影
三重视词义发展和同义词辨析
“词汇是发展的,词义是不断演变的”(论集p.);“不但词义具有系统性,词汇的组成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论集p.),①所以要用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观念看待古汉语词义、辨析古汉语同义词。
3.1词义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比如“先秦‘寺’有侍奉的意思,见于《诗经》《左传》和《韩非子》,只用于‘妇寺’或‘寺人’”;“秦代以后用宦官担任外廷的重要职务(九卿),于是把他们任职的官署称作‘寺’,如太常寺、大理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论集p.);“东汉以后,‘寺’的词义扩大,凡官署皆可称‘寺’”;“六朝以后,‘寺’一般只保留佛寺的意义”(论集p.)。不了解词义具有时代性,就可能以今律古,结果则似是而实非。
各个意义之间有内在联系的一词多义也是词义发展形成的。比如“行”,甲骨文的字形像十字路口,本义是道路;由“道路”引申为“走路”“行走”,由“行走”引申为“走了”“离开”,由“行走”还引申为“实行”,由“实行”再引申为“行使”“使用”。从本义到各个引申义,是慢慢形成的,因而具有时代性;各引申义之间具有不一样的关系,这构成了词义的系统性。词义的系统性是词的意义关系,词汇的系统性则是词际之间的关系。
3.2先生重视同义词辨析,并做了不少具体辨析工作。先生在同义词的辨析实践中,不仅重视辨析同义词之间在意义、用法、色彩等各方面的细微差别,而且尤其重视时空观念和系统性。
先生在同义词辨析中注意时空关系。例如:“军”和“师”都是集体名词,指军队,但“在先秦‘师’字一般指出征在外的军队,而‘军’字则不是。汉代以后,多用‘军’指军队,‘师’字逐渐很少用来指军队,‘军’字也就可以指出征在外的军队”(存稿p.34)。“‘之、适、如’都是到某地去的意思,它们是同义词,可能只是方言的不同”(存稿p.40)。②
先生在同义词辨析中注重系统性。例如:“执、秉、把、持、操”是词汇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组同义词,都有用手拿的意思,但它们的意义有细微区别。比如“执”的本义是捕捉俘虏或犯人,在它丰富的引申义中则蕴含着一个特点,即“把东西拿紧,把事物掌握牢固”(存稿p.77);而“‘秉’的词义特点不在于是否把东西拿得紧,而在于表示一只手从旁拿着东西,并附有小心地把东西拿平的意思,因此有‘秉公、秉烛’的说法”(存稿p.78)。③
①郭锡良《怎样掌握古汉语词义漫谈》。②郭锡良《同义词辨析十五例》。③郭锡良《漫谈同义词的辨析》。郭锡良先生与华学诚先生合影
四重视汉语同源词和音义关系
汉语同源词(同根词)的探求,关涉词汇系统性的研究,先生认为这是与同义词辨析一样值得重视的问题①;注意音义关系,做到音义互求,这是先生在研究实践中非常重视的。
4.1关于汉语同源词(同根词),先生是把它的产生与构词法之间的联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先生指出:“汉语的同源词是指有共同语源、音义都有一定联系的词;它的产生同汉语的构词法有密切的联系。它同西方语言学中不同语言中的同源词不是一回事,而是相当于西方一个语言中由相同词根派生出来的词。”(论集p.)词义构词、音变构词“始终是先秦重要的构词方式,同源词也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论集p.)。
词义构词法形成同音的同源词。先生认为,“近引申义是属于一词多义现象,远引申义就分化为同源词”(论集p.)。例如“道”,引申为“道理,规律”,引申为“述说”,就是远引申义,可以视为分化出两个同源词。同音的同源词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有的会产生分化字。比如“尊”,本义是“盛酒的器具”,引申为“尊崇,高贵”、“尊重,敬重”;后来为本义造了分化字,作“樽”作“罇”。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几个同音字似乎没有关系,“其实也是音同义近的同源词”(论集p.),如“才”“材”“财”之类(论集p.)。
音变构词法形成音近的同源词。比如“渴”“竭”“歇”这三个字的语音相近,“人缺水欲饮为渴,江河缺水为竭、为歇。水竭则尽,水歇则止,用于抽象事物为尽、为止”(论集p.)。如果语音差别大,即使意义相通,也不能视为同源词,如“屏、藩”(声母同为並母,耕元韵远)等。有人认为有一种“声韵同源”词存在,比如“莽”是“莫”的声母同源词,“夕”是“莫”的韵母同源词。先生认为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新奇说法”,因为它们“不符合音近的标准,也就是不符合音变构词的规律”(论集p.)。②
4.2先生说:“贯串各篇论文的共同思想是:汉语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既要继承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严谨学风和研究成果,又要吸收国外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论集p.2)③先生在词汇研究中注重以音求之,在语音研究中重视以义证之,注重音义互求,这些都是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特别是乾嘉以来语言研究的 传统的继承。
先生特别重视用历史发展的观念进行音义互求。利用音义关系讨论虚词的例子如:南北朝时期第三人称出现了新的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渠”。先生分析道:“大概是因为‘其’字发展到六朝有文白两读,文读随着之部其他字的读音演变了,而用作第三人称代词的白话读音却基本保存古代的读音,即跟来自鱼部的‘渠’的读音相近或相同了。”(论集p.13)④利用音义关系讨论实词的例子如:“‘饑’和‘饥’古音本不同,‘饑’是见母微部,‘饥’是见母脂部。意义分别也十分清楚。……[饑]是指年成不好,没有粮食吃。……[饥]是肚子饿,与饱相对。在上古文献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饑、饥’决不相混”(存稿p.43)。⑤等等。
结合方言讨论音义关系的例子如:有人认为“盖”字有见母覃韵上声读法,“?”是后人造的方言字。先生说:“‘盖’和‘?’是语义、用法有部分交叉而语音上并无联系的两个词,而且是古已有之的;它们在现代方言中的差别与它们的本义不同有关。”(存稿p.)“不管是指‘盖’这个词还是这个字,都不应有‘见母覃韵上声’这个音读”,“‘?’不是后造方言字。”(存稿p.)⑥
①郭锡良《怎样掌握古汉语词义漫谈》。②郭锡良《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③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序言》。④郭锡良《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先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渠’并非从‘其’演变过来的,而是跟‘伊’一样,同是方言词”。⑤郭锡良《同义词辨析十五例》。⑥郭锡良《从湘方言的“盖”和“?”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书影
五重视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中的问题
先生始终重视语言的系统性,重视语言的历时变异性等等,都是吸收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体现;先生认为,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要摈弃“三隔”,否则很难得出可信的科学结论,更是吸收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体现。
5.1先生对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的情况非常熟悉,并有深入思考,《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雷顿(J.Leyden)、孔好古(AugustConrady)等早期研究者的认识实际是从地域观念出发的,李方桂年发表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是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论证的最早论文;“从20世纪40年代起国内外对汉藏诸语言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原来据以提出论证的类型学的条件越来越失去作用”(存稿p.);白保罗(PaulBenedict)年出版的《汉藏语概论》,“推动了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但他是从同源词的角度来考察系属关系的,选材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任意性,缺乏严谨的对应规律,可信程度不高”(存稿p.)。先生说,“有人宣扬汉藏诸语言构成一个语系已经是常识问题,我却大不以为然”(存稿p.)。①
对汉藏同源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先生概括为“三隔”(论集p.)。
5.2音隔,“即从古音上说不通”(论集p.)。有人认为汉语的“壩”和藏语的“rags堤坝”是同源词,可以之证明汉语上古去声有*-s尾。先生反驳说:“先不管去声来自*-s尾的说法是否能成立。我们从声韵谈起,‘壩’是二等字,可以有个-r-,可是它的声母是帮母,跑到哪里去了?汉语‘壩’的上古音与藏语对得上吗?这就是音隔。”(论集p.)“说有*-s尾,也是一种音隔,形成双重音隔。其实‘壩’是后起字,始见于《集韵》,怎么可能有*-s尾呢?怎么会与藏语有同源关系呢?”(论集p.)②
5.3义隔,即“意义上有隔阂,比较的两个词意义上有差别,不宜相通,拐弯抹角,勉强凑合上”(论集p.)。有人认为“岁”与藏语的“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是同源词。先生说:“汉语‘岁’这个字词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表示岁星、岁时的意义。……汉历和藏历相差一两千年,汉语中由天文、历法的发展而产生的专用字词‘岁’,怎么会同藏文的skyod是同源呢?”“岁”有一系列意义,但“从来也没有表示‘时间之逝去’这样的意义,更没有‘行走’‘逾越’的意义。”(论集p.)③
5.4类隔,即“把借词算做同源词,我们就把它叫做‘类隔’”(论集p.)。有人认为汉语的“栋”和藏语的“gdung梁,栋材”是同源词。先生说:“‘栋’和‘梁’非一物,而且‘梁’本指木桥,引申为屋梁;它们是房屋建筑发展到相当高程度以后才会出现的文化词语。如果原始社会古人曾长期巢居或穴居,汉族和藏族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分开的时候,不可能出现这种科技词语。”(论集p.)④
①郭锡良《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
②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③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④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六重视先秦汉语词汇发展史
先生说,“我认为研究汉语史应该先把源头弄清楚”(论集p.2),所以先生不仅对先秦语法、语音有系统的研究,而且对先秦词汇发展史也有深入的探讨。
5.1众所周知,汉语词汇是由以单音词为主逐步走向以复音词为主的。那么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如何变化的,促成这些变化的内外部原因及其规律是什么,等等,就成为汉语史研究者长期探究的重大问题。先生从先秦汉语构词法入手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对汉语语法史、词汇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论断道:“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式也由单音词向复音词转变。周代就是汉语构词法发生这种重大转变的时期。”(论集p.)先生的研究证明:单音节语言创造新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词义构词,一是音变构词。西周以后出现了重要变化,“突破单音的格局、变革构词方式的动力,必然要在汉语内部形成”(论集p.)。“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复音词数量增加很大,成为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 个时期,此后结构构词成了汉语构词的主要方式”(论集p.)。
先生在研究先秦汉语构词法的过程中,有很多重要发现。比如甲骨卜辞的“偏正结构中用作修饰成分的词语范围还很窄”(论集p.);“上帝”之类“在殷商时代的词汇系统中还只能看作词组,最多也只能说是‘短语词’”(论集p.);与词汇密切相关的语音系统,周代“已经发展到十分繁复的局面”(论集p.);叠音词中除了音节重叠、意义与单字没有联系的一类之外,还有“黄黄”之类“与单音形容词‘黄’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论集pp.-);在联合式双音节词中,谓词性语素构成的复合词远比名词性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多,“这是由于谓词的语义比名词更具有模糊性特点所决定的”(论集p.)。①
5.2先生在先秦语法研究中,也涉及到不少词汇史问题。比如“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才逐渐产生了其他语气词”(论集p.59)②;“甲骨文中没有与‘之’‘兹’相对立的指示代词”(论集p.85)③;“战国中晚期以后‘於’已基本上取代了‘于’”(论集p.)④;“以”在甲骨文中是动词,“在西周金文中已虚化为非常活跃的介词,并有了连词的用法;春秋战国时期变化更大,主要作介词、连词,并进一步构成固定结构,转化成构词语素。中古以后介词‘以’逐渐衰落”(论集p.)⑤。
先秦时期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变化很大,“表示度量衡单位的名词形成了完整的系统,表示天然单位的名词也已产生,并日益丰富;增加了大量意义比较抽象的单音形容词,新产生了大量双音形容词”(论集p.);“到了周代,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从而形成了三类词多功能交错的局面”(论集p.),加上它们“在结合关系方面也有了发展”(论集p.),从而带来了词类活用、词的兼类现象的发展。⑥等等。
①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②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
③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
④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
⑤郭锡良《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
⑥郭锡良《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
《古代汉语语法讲稿》《汉字古音手册》书影七重视重词典编纂和词义概括性
郭先生在词典编纂方面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比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王力古汉语字典》里就融进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后来还撰写过《〈王力古汉语字典〉音读校勘记》(存稿pp.-)。郭先生在词典编纂理论上也有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对汉语辞书的编纂、汉语辞书质量的提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先生特别重视词典的义项问题,他说:“重视词义的概括性是应该的”(论集p.),如果不加概括地罗列义项,那就“总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论集p.);“按意义引申脉络排列义项,本该是词典处理义项的原则之一”,“如果真正要实现这条原则,恐怕首先要把汉语词汇史弄清楚,否则是难免不出错误的”(论集p.);要注意义项的同一性问题,即“一个字头下面的所有义项是不是都在语义结构系统的同一平面上,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论集p.),一词多义的各个义项、同源词义项和词素义义项,“这样三种不同性质的义项”,作为词典“应该有所区别”(论集p.)①。
关于辞书收字、关于辞书注音,关于《辞源》修订②、关于《汉语大词典》修订③、关于《汉语大词典》修订稿④,郭先生都曾发表过重要意见,本文不赘。
①郭锡良《词典义项处理漫谈》。②郭锡良《〈辞源〉修订方案(讨论稿)读后》。③郭锡良《在〈汉语大词典〉编纂修订方案讨论会上的发言》。④郭锡良《对〈汉语大词典〉修订稿的意见》。郭锡良先生参加年度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开班仪式
八结语
郭锡良先生年来到北京大学,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工作了32年,在古汉语教材编写、汉语语法史、汉语古音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先生在训诂词汇领域所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就,本文提炼出了七个“重视”,可以进一步总结为三个方面和四个特点。即内容有三个方面:宏观的重大论题、微观的具体研究、应用的词典编纂。其特点有四: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并重;系统性与历史变异性并重;同义词辨析与同源词探求并重;字词句落实与知人论世并重。先生在训诂词汇研究上取得的上述重要成就,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史的一部分。
研读先生的论著,我们还注意到很多文章都与古代诗文有直接关系。这些文章的写成,前后延续几十年,这说明先生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从来没有间断过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imaoa.com/bdzz/111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