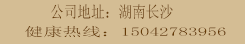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生活环境 > 流亡与还乡论普宁的主题兼及纳博科夫的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生活环境 > 流亡与还乡论普宁的主题兼及纳博科夫的

![]()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生活环境 > 流亡与还乡论普宁的主题兼及纳博科夫的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生活环境 > 流亡与还乡论普宁的主题兼及纳博科夫的
流亡与还乡
——论《普宁》的主题兼及纳博科夫的文化立场文/王立峰
摘要:在小说《普宁》中,纳博科夫塑造了一个看似举止可笑实则内心高贵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以及反讽、戏仿等修辞技巧的应用,将流亡的主题最终升华成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进而回应了浪漫主义时代以来就已经开启的还乡话题。小说的形式与主题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文本的深层内涵,其中不仅体现了纳博科夫的文化立场,更折射出他对历史及人类命运的思考。关键词:纳博科夫《普宁》流亡还乡文化立场《普宁》(Pnin)书写的是沉重的流亡主题,用的却是轻盈的喜剧性手法,这本身即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纳博科夫(VladimirVladimirovichNabokov,-)并非要通过普宁这个人物发起政治控诉,为他自己和其他俄国流亡者鸣不平,也无意讽刺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和趣味。他思考的是一种人类更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即高贵的心灵如何在混乱无序、价值失范的现代世界寻得安身立命之所在?相对于政治上的流亡,纳博科夫更关心精神上的还乡,这是一个在早期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启的话题,而纳博科夫尝试用他的艺术做出回应。
《普宁》英文版封面(Vintage)01
喜剧效果的生成与消解
纳博科夫制造笑料的方式十分简单,那就是竭力突出普宁的俄国教养和美式文化间的摩擦:
那位上了年纪的旅客,坐在风驰电掣的列车靠北窗户的位子上,对着两个空位子,身旁也没人坐,他不是别人,正是铁莫菲·普宁教授。他头秃得挺像个样儿,皮肤晒得黧黑,脸蛋也刮得蛮干净,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褐色的大脑袋,那副(遮住开始脱落的眉毛的)玳瑁边眼镜,猿猴那样厚实的上嘴唇,滚粗的脖颈和那穿着绷得挺紧的花呢上衣的、结实的身子骨儿;但临了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他那(眼下穿着法兰绒裤子、交叉着的)两条腿却挺瘦,脚也显得纤弱无比,几乎跟娘儿们的(feminine)脚一模一样。(《普》4;Pnin4)
小说开篇就赋予了普宁一个可笑的形象,壮实的上半身与纤瘦的下半身制造出不和谐的视觉效果。似乎是为了加深文体的喜剧效果,中文译者在翻译时,将中性的“feminine”译成了略显粗俗的“娘儿们的”,看似将普宁推向了一个更为可笑的境地,实际上却多少破坏了作者有意营造的不动声色的叙事口吻。更可笑的是眼下安坐在火车上,赶往温代尔以西两百俄里外的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做讲演的普宁,实际上坐错了车,原因就在于他“跟许多俄国佬(Russians)一样,过分喜好时间表、地图、目录这类玩意儿,尽量把它们收集齐全,然后带着无事瞎忙的兴奋劲儿,随心所欲的利用它们,一旦给自己推敲出一些时间表就沾沾自喜”(《普》4;Pnin4)。可惜,普宁精心设计的出行方案,却是建立在一份五年前的火车时刻表之上,因而并不适用。如果一个定居美国十几年的俄国流亡者在计算距离时,仍然不自觉地用俄里(verst)而不是英里(mile)作为度量单位,那么他的在地化(localization,也译本土化——编者按)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所以,过时的不是火车时刻表,而是普宁俄国式的习惯,尽管他试图在外貌举止上更加美国化,以更快地融入美国东部的中产阶级社会,但是俄国气质与日光浴和美式着装的结合只能产生喜剧效果。
在外捕蝶的纳博科夫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更难以克服的障碍是语言,这也是引起普宁焦虑的主要根源。初到美国的普宁对英语一窍不通,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他的英语总算到达了可以与人沟通的程度,然而阅读与写作依然糟糕,口语也保留着浓重的俄国口音,“如果说他的俄语是音乐(music),那么他的英语就是谋杀(murder)”(《普》75;Pnin47)。在做学术报告时,普宁会事先用俄语准备讲稿,再“把他那充满格言警句的流畅的俄文稿费劲地译成破绽百出的英文稿”(《普》10;Pnin8)。对于普宁这样仍旧无法熟练掌握英语的流亡者而言,不能以俄语言说,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文化与思想层面的表达遭到了限制,作为个体的完整性受到了侵犯,更意味着他们会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切实的挫折,意味着被嘲笑、被误解,意味着不公与不幸会经常地光顾他们的命运。因此,我们不禁会怀疑,将小说的喜剧性建立在文化差异,建立在俄国特质与美国文化的对立上,对于普宁这样的流亡者而言是否过于残忍?
当一种文化凭借其强势的地位压抑他者文化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相应的价值判断则是霸权的衍生产品,其可靠性就有待商榷。普宁在温代尔学院上演的种种喜剧故事,他迂腐的言谈、可笑的举止、笨拙的行为,究竟是他真实个性的体现,还是傲慢与偏见的产物?对此,作者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小说的第五章描述了普宁在俄国流亡者聚会上的表现,给了他一个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中一展身手的机会。于是,那个在学生面前神神叨叨的可怜教授,在图书馆爬梳匪夷所思的历史细节的迂腐学究,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谈吐风趣的体面人,他对《安娜·卡列尼娜》的种种细节如数家珍,知识与智慧的光芒在他身上熠熠生辉(Pnin90-91)。在饭后的槌球游戏(Croquet)中,普宁又从一个“动作慢吞吞、笨手笨脚、很有点僵硬的人,一下子变成一个活蹦乱跳、默不出声、面带狡猾神情的驼子”(《普》;Pnin96),他展现了其他时候难得一见的灵巧,击球的动作不但精确,而且优雅。在槌球游戏这个场景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留意,普宁参加游戏前,特意换上了一条百慕大短裤,一种裤长到膝盖上方2、3厘米的短裤,因此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普宁在着装方面的美国化既没能让他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又引起了同胞们的侧目,真可谓两头不讨好。
普宁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截然不同的表现,足以用来质疑对他嘲笑的正当性。除此以外,作家又通过叙事视角的转变,进一步追问叙事本身的可信性,并最终彻底消解普宁行为的喜剧效果。小说采用了被热奈特(GérardGenette)称作“赘述”(paralepsis,又译作多述)的叙事手法(Toker)。“赘述”原本是指 人称的叙述者,违背模仿逻辑,讲述他本不应该知道的内容(热奈特)。以《普宁》为例,小说前六章在讲述普宁的故事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因此他对普宁的身体状况、心理活动、个人经历都洞若观火。但是,在第七章中,叙述者突然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变成了小说中活生生的人物,开始用受限制的视角讲述普宁的故事,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赘述”现象。“我”作为小说人物的叙述摧毁了前六章叙述的可靠性,因为原则上,“我”掌握的信息不可能达到前文所展现的那种程度。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怀疑,普宁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传闻与流言构成的小道消息。
小说的结尾尤为巧妙,考克瑞尔(Cockewrell)这位在温代尔学院以模仿普宁著称的英语系主任,对“我”绘声绘色地讲述普宁在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发表讲演,却发现自己带错了讲稿的故事(Pnin)。这无疑是在告诉读者,关于普宁的故事都是“我”听来的,既不是亲眼所见,更不可能全知全能的掌握一切细节,因而它的真实性是成疑的。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拨开文字表层的情感色彩,普宁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副形象。他对学生讲授俄国文学时忘乎所以的态度,无非是源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他迂腐冬烘的研究实则是对知识的敬畏;他待人接物时的笨拙木讷完全是诚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他对于初恋以及前妻的态度则反映了他善良高贵的本质。
纳博科夫年春天在剑桥纳博科夫选择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制造普宁的笑料,以一种轻盈的方式淡化了流亡主题的政治性因素,随后他又煞费苦心地通过“赘叙”的方式解构了故事的可信性,同时也消解了普宁身上的喜剧效果,还原了普宁高贵的形象。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假如我们并不认为自己与普宁的同事相比智力上更优越,那么普宁为什么不能在他的同事间获得公正的评价——就像他在读者中已经获得的那样——而仍然要遭受嘲笑,乃至离职的命运?换言之,为什么普宁的高贵不被人理解,他面临的真正困境究竟是什么?
02
从政治流亡到精神还乡
纳博科夫是一个高度自觉的艺术家,也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他反对说教、反感寓言、厌恶政治,将个人风格视作作家最重要的特质(Appel19)。《普宁》不是他 次触及流亡者的生存状态这一主题,但是现实政治却从未真正占据他文学的中心,相比于政治流亡,纳博科夫更关心精神还乡。
流亡对于纳博科夫本人来说, 的困扰在于放弃俄语,转而用英语写作。早在年,艾德蒙·威尔逊(EdmundWilson)就称赞纳博科夫的英语好得令人惊艳,既精妙又完整,足以与康拉德(JosephConrad)并列(Karlinsky49)。但纳博科夫不为所动,坚持认为放弃他无拘无束、丰富多彩、得心应手的俄语,代之以二流的英语,是他个人生活中 的悲剧(Lolita)。年,早已凭借《洛丽塔》(Lolita)名动天下的纳博科夫,仍然向来访者表示,自己因为不能再用俄语写作感到痛苦,不得已只能把英语当作一种怅然若失的代替品(Appel41)。纳博科夫的俄语可能并没有他声称的那般精妙,他的英语也未必如他描述的那般不堪,在这方面我们无须过分信赖他的自我评价。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这种自我评价背后流露出的心态,那就是对精神故乡失落的哀叹。
年,7岁的纳博科夫与父亲在圣彼得堡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而言,纳博科夫只有在流亡美国的初期感受过生存的压力,此后的美国岁月尽管偶尔也会遇到经济困窘的时刻,但总体而言是更自由、更安全的。他可以在假期到处游历,研究蝴蝶的同时写自己的小说。康奈尔给了他一份教职,《纽约客》不时刊登他的稿件,当时美国执牛耳的批评家威尔逊和他也有不俗的交情。然而,现实生活的安稳并不能抚平纳博科夫文化上的失落感,因此他在精神上始终都是一个异乡人,永远渴望还乡之旅。
悲哀的是故乡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精神上,纳博科夫都失去了还乡的可能。普宁又何尝不是?流亡者的聚会只能让他偶尔重温熟悉的旧时光,日常生活中的挫折与痛苦才是常态。博伊德(BrainBoyd)在他 的《纳博科夫传》中提醒我们普宁与堂吉诃德之间的关系,在写作《普宁》之前,纳博科夫正在哈佛大学讲授这部 的西班牙小说。纳博科夫认为塞万提斯的小说“构成了一部以残酷性为主题的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堂吉诃德讲稿》63),他对堂吉诃德被残酷对待非常不满,更愤愤于评论者将小说视作幽默的、富有同情心的作品,所以他用普宁的流亡生涯戏仿了堂吉诃德的骑士之旅。如同堂吉诃德一样,普宁不断遭遇痛苦:去女子俱乐部演讲却坐错了车;刚找到合适的住处却又要搬家;被前妻抛弃而后又遭到利用;参加俄国流亡者聚会却差点迷路;本以为能获得温代尔的终身教职却发现随着保护人哈根(Hagen)离职,他的职位也被取消了。这些都令我们想到堂吉诃德所遭受的虐待与痛苦,甚至他的名字(Pnin)本身就意味着“痛苦”(pain),两者之间读音非常接近,尤其是当普宁用俄国口音的英语发这个音时(博伊德)。
然而,普宁遭受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他愚蠢、邪恶、卑鄙、堕落,只是因为他处在一个不能理解他的高贵的世界中,就像堂吉诃德的挫折并不缘于他缺乏骑士精神,相反是因为他在失落了骑士精神的世界中表现得过于富有骑士精神。纳博科夫让我们意识到,个体的偏见和冷酷,世界的无序与混乱,才是造成普宁痛苦和不幸的根源。流亡只是一个楔子,目的是引入对个体生存状态的追问。虽然对大部分现代人而言,流亡是一种未曾亲历过的极端生存状态,但是只要永恒的公平与正义未曾降临 ,混乱与无序就仍然是世界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人都是流亡者,都将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堂吉诃德》讲稿,[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纳博科夫并没有让普宁陷入绝望的境地,而是给了他解脱的希望,希望正在维克多·温德身上。维克多是普宁前妻丽莎和埃里克·温德的儿子,是第二代流亡者。维克多是一个安静早熟,有着出色艺术天赋的少年,与温德夫妇没有任何共通点。实际上,纳博科夫暗示我们,维克多与普宁之间才是精神上的父子。在第四章的开头,纳博科夫让维克多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他的父亲是一个孤独的国王,在海滩上来回踱步,等待着美国冒险家的搭救,从此开启流亡的生涯(Pnin61-63)。而在这一章的结尾,普宁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从宫殿中逃离,在荒凉的海滩边等待大海另一边的神秘船只前来救援。普宁与维克多分享了同一个梦境,普宁是维克多想象中的父亲,两者之间的精神纽带超越了血缘的限制。
纳博科夫并不承认乔伊斯(JamesJoyce)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影响,然而50年代初他在康奈尔讲授欧洲文学时,又曾专门讨论过乔伊斯,并且详细分析过斯蒂芬(Stephen)与布鲁姆(Bloom)之间的双重梦境(《文学讲稿》)。因而我们很难不去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普宁与维克多之间的关系。
乔伊斯小说中人物命运是相对“静止”的,布鲁姆与史蒂芬即便“发现”了对方,也很难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与维克多的命运却是“流动”的,不仅充满艺术天赋的维克多未来可期,就连失去教职的普宁也没有陷入彻底的绝望。诚恳、高贵、善良的普宁最缺乏的就是艺术气质和想象力,所以他无法通过艺术的方式重构精神的故乡,只能在回忆里寻求安慰。但回忆是不可靠的,它可能会消散,也可能被改写,故事的 ,普宁拒绝了“我”以“最诚恳的措辞”(Pnin)发出的邀请,不愿接受继续留在温代尔任教,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侵犯了普宁的记忆。“我”对普宁儿时经历,他的父亲及前妻的讲述冒犯了普宁,因为这些回忆是身为流亡者的普宁与古老俄国之间 的纽带,是他得以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他宁愿失去教职,也不愿意与“我”为伍。大卫·考沃特据此认为,与纳博科夫相比,普宁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不是一个艺术家,只有通过艺术,流亡者继承的回忆才能被唤回并赋予超越乡愁的意义(Cowart)。
普宁的弱点恰好是维克多的强项,早在儿童时期,维克多就对光线充满兴趣,并且对色彩与光线引起的感官变化十分敏感(Pnin71-72)。这在纳博科夫本人的评价体系中,几乎是 别的赞美了(Appel19)。维克多弥补了普宁的缺陷,也为普宁重启精神上的还乡之旅提供了可能性。普宁对此可能有些懵懂,因为他不能理解艺术的价值,就像他不清楚维克多送他的那个玻璃碗的真正价值一样。不过在普宁兴高采烈地举办的温居宴会的 ,当他从哈根教授口中得知自己的职位已经不保,因而有些失神的时刻,那个失手滑落的胡桃夹子并没有砸到水池里维克多送的玻璃碗。我们有理由相信,普宁会带着维克多送的玻璃碗离开温代尔,终有一天,他会明白这个碗的价值,并且真正体会到维克多给他生命带来的意义。普宁是不幸的,他不得不承受生活中的痛苦,面对流亡带来的精神创伤和现实挫折,他无法通过艺术为自己赢得出路。幸好维克多的出现给了他以慰藉,使他在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中不再孤身一人,而他又以自己高贵的心灵护卫着维克多的成长,在这一点上,两人无疑又都是幸运的。
《普宁》英文版(Penguin)03
作为治愈手段的艺术
回顾纳博科夫的一生,他的人生与他的文学正好位于两个极端。在纳博科夫的生命里,十月革命、世界大战、流亡、纳粹等都是沉重的话题,可是在他的文学中,多的是轻盈的头韵,顽皮的双关语,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文字游戏。一言蔽之,纳博科夫沉迷于文学形式的建构(《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6-12),并试图赋予这形式永恒的意义。纳博科夫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是疏离的,在他笔下很难寻觅到期待中的——假如这是一种合理的期待的话——悲天悯人的历史关怀。声音、光线、色彩以及这些元素带给人的感官体验才是纳博科夫描述的重点,与之相对的,结构、细节、象征而不是寓言、说教、政治控诉构成了他小说最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对文字细节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imaoa.com/bdjt/10777.html